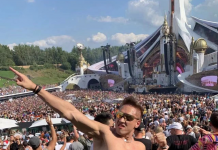马来西亚民族融合的问题真这么严重?
这个问题的解题思路在于所处背景。
如果说,改名换姓尚且是小事(一些地方本来就有婚后冠夫姓的传统),那与原本家庭几近断绝关系,就让很多父母无法接受。
怎么就断绝关系了?
大的不说,于“猪肉”,两宗教就水火不容。而这又是大多数华人日常的传统食材。
更重要的是,南洋华人多来自闽粤一带,宗族观念强,改教后逢年过节不能拜祭先祖,无法为父母送终,大逆不道又加一层。
朋友说,峇峇娘惹的出现,不得不提一个地方——马六甲。
那是郑和五下西洋的所到之处,也是最古老的华人据点之一,闻名遐迩的马六甲海峡,就以这座城市命名。
为了更好了解这个问题,我决定去一趟马六甲。

从吉隆坡坐大巴到马六甲,要2个小时。
从马六甲郊区的中心车站到古城,还要10分钟车程。
下午四点多,烈日已力有不逮,我决定沿着导航的路线,向着几公里外的市中心步行前进。
沿途安静得惨人,除了经过的一排像永旺、莲花之类的大商场人气旺盛,商场外的街道上路人寥寥,与吉隆坡的热闹大相径庭。
但沿途所见,马六甲的房子还是很有特色的,尤其是那些排屋。

尤其是很多房屋采取亮色——彩色的外墙,给人色彩鲜明的感觉,而那些色彩鲜明和这里的天气搭配得刚刚好。
整个小城市给人的感觉就是破破旧旧,但是很有感觉——不是穿梭回到过去,而是一种过去的历史厚重感和现代的人类交织在一起。
1405~1433 年间,明成祖曾派郑和七下西洋。
郑和几乎每次都到马六甲,而部分随从就此落地生根,也把中国习俗带到当地。
此后,作为荷兰的前殖民地,又到英殖时期,日据再到回归大马,现在马六甲可以见到欧式的、清真式的、中式的各种建筑错落分布在一起,很有特色。

蜿蜒而过的马六甲河将城市南北分隔开来,河流往西的尽头就是大海。
看着脚下如今不到20米宽的马六甲河,很难想象当年郑和下西洋的情形。
从马六甲国际科技学院拐过一条小路,我一头撞进了周日的鸡场街夜市。

这是马六甲每个周末的热闹集市。
一路走过,各种摊贩沿着狭小的街道两侧摆卖炒粿条、叻沙、果汁与各种小工艺品,与其他城市的夜市并无两样。
如果说有差别,那就多了一些独有的小吃,夹在两片叶子间的烤鱼肉,随处可见的娘惹糕点,以及煎蕊(一种刨冰甜点)。
这些小吃的特色,也是这个城市的特点。
炒粿条是闽南人的日常食物,叻沙是马来人的爱,而糕点和煎蕊则来自娘惹(两个民族融合的产物)。
很难说这些食物是如何杂糅到一起共生的,但在这里,似乎一点不违和。
倒是沿街的华人会馆,让华人宗族传统坚强的生命力让人一览无遗。
两三公里长的一条鸡场街,我路过了至少十来家华人会馆,福建会馆、海南会馆这种自然不说,还有类似增龙会馆、永春会馆,乍一看无法按图索骥的。

飞檐、雕梁画柱、门神,乃至会馆里供奉的神像,一个会馆,就是一个派系,当连接的亲情来到异国他乡,抱团是顺势而为,也是不得已而为之。

鸡场街热闹到了晚上10点才有点偃旗息鼓的意思。
除了这条街,就剩沿河的酒吧街还灯火犹存。
如果说古城是马六甲的一副面孔,那当古城的店面几乎都关门后,马六甲的面孔则到了古城之外。

沿途走过,酒吧门口揽客的印度小哥不断朝我投来殷切的目光。不时有河上观光船驶过,一船人好奇地张望着两岸贫瘠的景观。
当我从绵延2公里的沿河酒吧街走了出来,顺着夜深人静的骑楼街道,又一路到了马六甲科技学院。
惊喜发现,这边原来还有也有一个印度人聚集的小型夜市。
空旷的场地里小贩们支起栏杆就摆卖衣服,或者随意地将所有款式的鞋子平铺在地上。
价格便宜得渗人,衣服标价10马币、20马币的样子,让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是否是二手货。

一堆印度人坐在最靠里面的几个小吃摊位前,喝着玻璃大桶里购买的那些色彩鲜艳的饮品,就着音响里的动感音乐,闲散地聊天。
相比鸡场街的热闹与熙攘,这里有另一种让人沉迷的氛围。
“现在人们都不住古城了,基本都住外面。”一个华人阿姨说,如果想逛街买东西,可以去一公里外的英雄广场。
广场的顶上有个英雄草场,本地人晚上喜欢在草坪上坐着吹风聊天。

至今600年,华人是分三波移民到马来西亚。
最早的一波人正是郑和时期,基本都是单身的男性,来到了马六甲。
之后这些男性就和本地女性结婚,他们的后代就是峇峇(男孩)娘惹(女孩)。
这些在马来西亚本土出生的华人,平时说话都是马来语中掺杂着一些中国的方言;就连一日三餐、穿衣打扮等各种生活习惯中都可以看到中华文化的影子。
然而,本想左右逢源却也容易两头不讨好。
“早期的峇峇人是矛盾的一群,他们脱离华人社会,却又不能真正融入马来社会,成为两头不着岸的人。”当地朋友告诉我。
“我们如今把他们当作一个族群还是一个社会现象在讲?”朋友反问。
如果是族群,没有娘惹这个民族,如果是个现象,那么他们的出现,是不是也是时代的产物?
可供佐证的是,峇峇娘惹有段时间被归为土著身份,可后来又由于政治因素,被重新归为华人。
从某种程度上,很多峇峇娘惹自小进入西式教育体系,改信基督教,也很难被宗祠文化构成的华人群体所吸纳。
乃至现在,与“娘惹”比起来,峇峇似乎被忽略了。
“可能从潜意识里,你就觉得他们低人一等,特别是女性身份的娘惹,更具有一种可供把玩的暗示。”朋友对此倒是直言不讳。

毫不意外,作为一个硬币的两面,这种民族的融合,带来了亲切感也会带来疏离感。
这种感觉,就像很多年后,我在古城里的街头看到“脚车出租”的招牌,突然有种既亲切又好笑的感觉。

自我离开老家后,我已经很多年没遇到“脚车”这个闽南方言里自行车的说法。
而当它从俚语转换成文绉绉的文字表达,突然让人有种土气与文雅相互融合的混乱感。
此类的词汇并不少,同样的还有“罗哩”,纯正的中文说法是“卡车”,南洋华人直接将英语“lorry”音译,并回流闽南,口口相传,成为我童年里的词汇之一。
在打金街的一家摆卖瓷器和画作和工艺品店,我对一幅画作突然感兴趣。

这幅画夹带着闽粤沿海小孩的观感,一看就对上眼,太可爱。
朋友问我喜欢什么,我说,我就喜欢他拉屎拉不出的专注和眉头紧锁,与一丝不苟的发型,相映成趣。
这大概,也是这种混乱的疏离感所致。
(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城南八卦局) |